堂兄弟定義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英)理查德·道金斯寫的 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訂版) 和詹姆士.道斯的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中信 和立緒所出版 。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劉柳書琴所指導 白春燕的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 (2020),提出堂兄弟定義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新劇、文化劇、社會網絡、演劇系譜、新文化運動、台灣文化協會。
而第二篇論文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釋澈定薛華中博士所指導 陳紀南的 齋醮在台灣發展演變之研究一兼論台北碧潭地區四大古寺院導師之卡理斯瑪現象 (2014),提出因為有 卡理斯瑪現象、齋教、齋堂、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的重點而找出了 堂兄弟定義的解答。
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訂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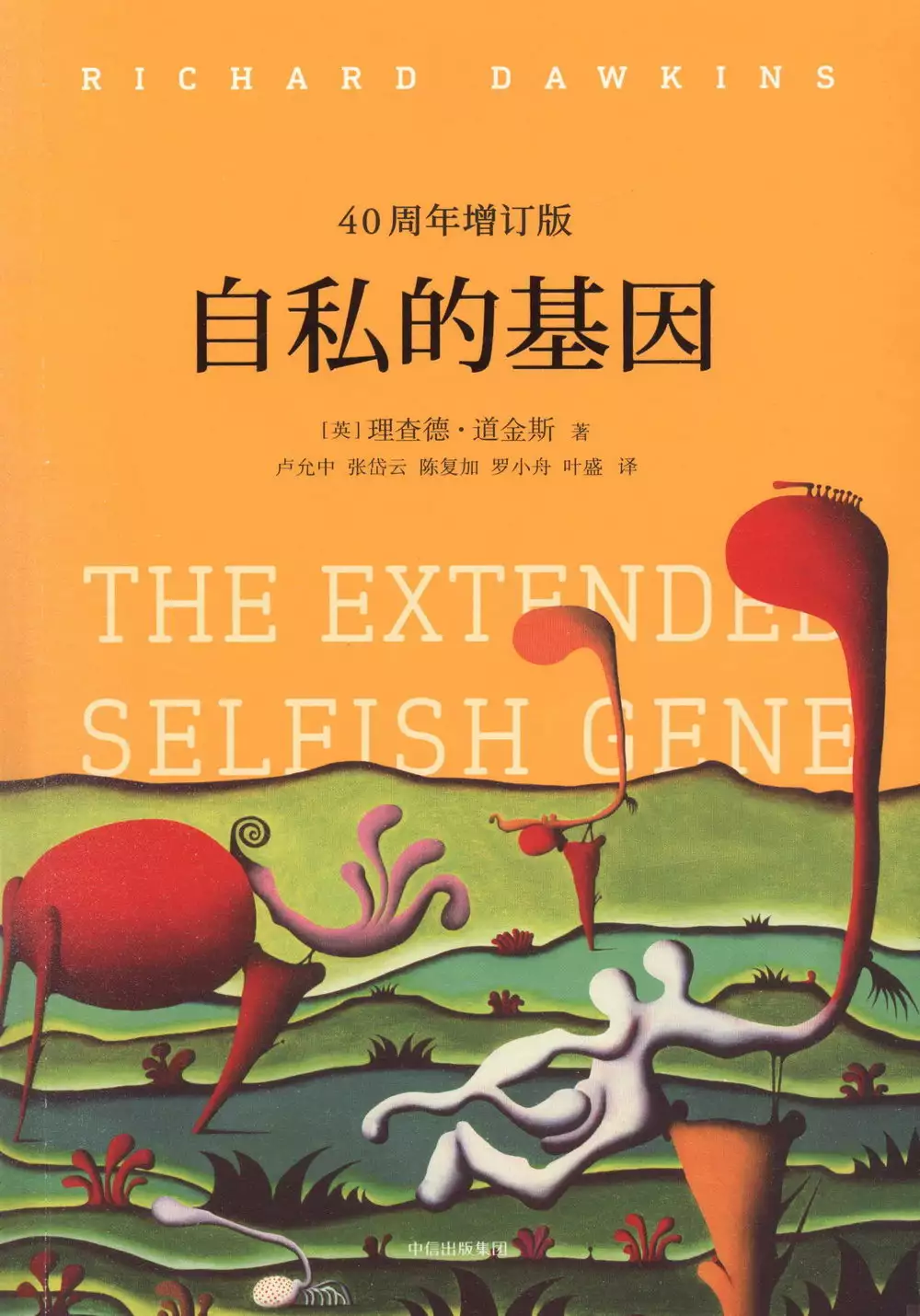
為了解決堂兄弟定義 的問題,作者(英)理查德·道金斯 這樣論述:
《自私的基因》于1976年初版之後便暢銷全球,是20世紀百大經典名著之一,是一部不僅在基因領域更在社會科學領域具有顛覆性、革命性的經典作品。我們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生命有何意義,我們該如何認識自己?《自私的基因》以充滿想象力的敘述回答了這些重要命題。 道金斯在本書中提出大膽創見:我們生來是自私的,任何生物,包括我們自己,都只是求生的機器。這本書是實實在在的認知科學,複製、變異和淘汰簡單的三種機制可以演變出大千世界所有生命現象的林林總總。《自私的基因》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世界觀。道金斯在書中將進化論從基因層面升華至文化層面,創造了「覓母」(「meme」,即文化基因)這一新型的複製基因名詞
,特指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文化進化,並提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我們人類,能夠反抗自私的複製基因的暴政。《自私的基因》出版之後,在社會各界引發了重大爭議。 本書為40周年增訂版,在30周年版的基礎上,道金斯新增兩章內容回應爭議和誤解,其中第14章《基因決定論與基因選擇論》解決了「偉大的基因決定論謬誤」—這是一種錯誤的解讀,認為我們的行為完全是由我們的基因來決定的,而與環境或其他因素無關。第15章《對於完美化的制約》解決了「偉大的適應論誤解」—即所謂「適應論者」所持有的觀點,認為生物的所有性狀和行為都應被理解為適應性。新增的兩章內容共計六萬餘字,更加完善了道金斯對於「自私的基因」的經典論述,形
成這本特別的「延伸的」40周年紀念版《自私的基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首席西蒙尼「公眾理解科學教授」,進化論生物學家。他是英國著名科學作家,幾乎每本書都是暢銷書,並經常在各大媒體引起轟動。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會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選出在世的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道金斯赫然在列。 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他的基因觀念顛覆了我們對自身的幻覺,深刻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其他主要作品有《延伸的表型》《祖先的故事》《盲眼鐘錶匠》《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解析
彩虹》《魔鬼的牧師》《攀登不可能的山峰》等。 40周年增訂版說明 40周年增訂版序言 30周年版簡介 第2版前言 序言 前言 第1章 為什麼會有人呢? 好奇的孩子常會問:“ 為什麼會有人呢?” 達爾文使我們能夠在面對這個問題時,給出一個切合實際的回答。生命有意義嗎?人生目的何在?人是什麼?我們在面對這些深刻的問題時,無須再求助於怪力亂神。 第2章 複製因數 它們存在於你和我的軀體內,它們創造了我們,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心靈,而保存它們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這些複製因數源遠流長。今天,我們稱它們為基因, 而我們就是它們的生存機器。 第3章 不朽的螺旋圈 DNA 分子因其
太小而不能為肉眼所見,但它的確切形狀已被人類用間接的方法巧妙地揭示了出來。它由一對核苷酸鏈組成,兩條鏈相互交織,呈雅致的螺旋形,這就是“ 雙螺旋”或“ 不朽的螺旋圈”。 第4章 基因機器 北極熊基因可以有把握地預先知道,它們尚未出生的生存機器將會面對一個寒冷的環境。這種預測並不是基因進行思考的結果。它們從不思考:它們只不過是預先準備好一身厚厚的皮毛,因為在以前的一些軀體內,它們一直是這樣做的。 第5章 進犯行為:穩定性和自私的機器 對於生存機器來說,合乎邏輯的策略似乎是將其競爭對手殺死……。儘管自然界會發生屠殺和同類相食的現象,但認為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卻是對自私基因理論的一種幼稚的理解。
第6章 基因種族 根據漢密爾頓的遺傳學說,我們很容易解釋氏族之間的仇殺和家族之間的爭鬥。亂倫的禁忌表明人類具有深刻的親緣關係意識, 儘管亂倫禁忌在遺傳上的好處與利他主義無關。它大概與近親繁殖能產生隱性基因的有害影響有關。 第7章 計劃生育 個體之所以調節其窩卵數,絕非出自利他性的動機。它們不會為了避免過多地消耗群體的資源而實行節制生育。它們節制生育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它們現有子女的存活數,它們的目標同我們提倡節制生育的本來目標恰好背道而馳。 第8章 代際之戰 這是一種微妙的爭鬥,雙方全力以赴,不受任何清規戒律的約束。幼兒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欺騙。它會裝成比實際更饑餓的樣子, 也許裝得比實際更年
幼或面臨比實際更大危難的模樣。另一方面, 父母必須對這種欺騙行為保持警覺,盡力避免受騙上當。 第9章 兩性戰爭 鑒於精子易於散失,雄性魚必須等到雌性魚產卵後才在卵子上射精。但這樣,雌性魚就有了難得的幾秒鐘時間可以趁機溜走, 把受精卵丟給雄性魚照管,使之陷入特裡弗斯所說的進退兩難的境地。 第10章 你為我撓癢,我就騎在你頭上 假設B 頭上有一隻寄生蟲,A 為它剔除掉。不久以後,A 頭上也有了寄生蟲,A 當然去找B,希望B 也為它剔除掉,作為報答。結果B 嗤之以鼻,掉頭就走。B 是個騙子,這種騙子接受了別人的恩惠,但不感恩圖報。 第11章 覓母:新的複製因數 我認為就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最近出
現了一種新型的複製因數。它就在我們眼前,不過它還在幼年期,還在它的原始湯裡笨拙地漂流著。但它正在推動進化的進程,速度之快令原來的因數望塵莫及。這種新湯就是人類文化的湯。 第12章 好人終有好報 好人的數目註定要減少,善良在達爾文主義裡終將滅亡。這裡的“ 好人”還有另一種專有解釋,和俗語中的含義相差並不遠。但在這種解釋裡,好人則能“ 得好報”。 第13章 基因的延伸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理:一個生物體內的基因可以對另一個生物體有延伸表型影響。基因從其自身身體中逃逸出,操縱著外部世界。 第14章 基因決定論與基因選擇論 若干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和神學家們一直都在爭論決定論觀點是否正確,以及它與一
個人為自身行為所需承擔的道德責任之間是否有關聯性。 第15章 對於完美化的制約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動物很有可能是“過時的”,影響其建立過程的那些基因是在某個更早的時期為了應對與今天不同的條件而被選擇出來的。 章節附註 參考書目 第14、15章術語表 評論集萃 40周年增訂版序言 科學家與政客不同,能夠以錯為樂。政客如果改變了主張,會被人說成是“ 反復無常”。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就誇口說自己“從未開過倒車”。科學家一般來說也願意看到自己的觀點被證明是正確的, 但是偶爾一兩次的錯判同樣能夠為自己贏得尊重,尤其是當他們能夠優雅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時。我從未聽說過有
哪位科學家被指責為反復無常。 在某種意義上,我很願意找到一種方式來收回《自私的基因》一書的核心思想。在基因組學的世界中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多激動人心的事情, 那麼一本出版於40 年前的以基因為題的書如果還不至於被徹底摒棄的話,必然需要接受大幅度的修改—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很是誘人。然而在這本書中,“基因”的定義比較特殊,它是為進化量身定做的,而不以描述發育問題為目的—若非如此,這本書就真要大改特改了。 本書中基因的定義來自種群進化生物學家喬治·C. 威廉斯, 他已然仙逝,但無疑是本書的英雄。同樣離我們而去的還有約翰·梅納德·史密斯和比爾·漢密爾頓。威廉斯認為:“基因是染色體材料上任何一個
可能存在得足夠長久的代際,並且是可以當作自然選擇的單位的部分。”我從這個定義中得出了一個多少有些好笑的結論:“嚴格來講,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染色體有點自私的一大部分以及更為自私的一小部分》。”胚胎學家關心的是基因會如何影響表型,我們新達爾文主義者的關注點則是實體在種群中的頻度發生的改變。這些實體在威廉斯看來就是基因(威廉斯後來稱之為“ 抄本”)。基因是可以計數的, 而其出現頻度是其成功與否的一種測度。本書的一個核心思想是:生物個體不具備上述討論的基礎。單個生物體的基因頻度都是100%,因而無法“ 當作自然選擇的單位”。同樣,複製單元也無法扮演這樣的角色。如果非要說生物個體是自然選擇的單位,
這其中的意味也很不一樣,實際上是把生物個體視為基因的“ 載具”。生物個體成功與否的測度是其所攜帶的基因在未來代際中出現的頻度,而其奮力去爭取最大化的那個量值是漢密爾頓所說的“廣義適合度”(inclusive fitness)。 一個基因要獲得這些數值層面的成功,就需要在生物個體身上表現出表型效應的價值來。一個成功的基因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表現在許多個體身上,它能夠幫助這些個體在環境中存活得足夠長久,令繁育下一代成為可能。不過,這裡的環境指的並不僅僅是身體之外的外部環境,諸如樹木、水體、天敵等等,其實還包括了內部環境,特別是其他基因—自私的基因與其他基因共用了一系列生物個體的身體,不僅遍佈種群,
而且跨越代際。由此,必然的結果是,自然選擇會青睞那些在有性繁殖種群中其他基因的陪伴下共同繁榮的基因。從本書的主張來講,基因的確是“ 自私的”。但基因同時也能夠與其他基因合作,它們所共用的不僅僅只是某一個特定的生物體的身體,還是這個物種的基因庫所產生出來的一般意義上的所有身體。 一個有性繁殖種群是由相互相容、彼此合作的基因所組成的聯合體—它們今天會合作是由於許多世代以來在先祖類似身體中的合作已經讓它們得以繁榮。需要瞭解的重點在於(這一點常常被人誤解),合作性之所以得到青睞,並非是因為一組基因天然地作為一個整體接受選擇,而是因為單個基因是單獨接受選擇的,但這個選擇過程的背景是該基因在身體內有可能
接觸到的其他基因,也就是說物種的基因庫內的其他基因。一個有性繁殖物種的每一個個體都是從基因庫中抽取自己的基因的。在一系列個體的身體裡,這一物種(而非其他物種)的這些基因會不斷地彼此相遇,彼此合作。 我們仍不完全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推動了有性繁殖的起源。但是有性繁殖的一個結果就是,物種可以被創新性地定義為:相互相容的基因所組成的合作聯合體的棲息地。正如在《基因的延伸》這一章所指出的: 合作的關鍵在於,對於每一代而言,一個身體裡所有基因共用的那個去往未來的出路如同“ 瓶頸”一般—那是它們渴望搭乘著前往下一代的精子或卵子。“ 合作的基因”也是一個同樣恰當的書名,而且如此一來, 這本書就根本不用做任何
修改了,我估計人們因誤解提出的許多質疑也可以因此而避免了。 另一個不錯的書名是“不朽的基因”。“不朽”比“自私”更有詩意,同時也抓住了本書的一個關鍵性問題。DNA(去氧核糖核酸)複製的高保真度對於自然選擇而言是一個基本要素,也就是說突變是罕見的。高保真度意味著,基因作為準確的資訊拷貝能夠存續數百萬年之久, 成功的基因如此,不成功的基因則不行—而這正是成功性的定義。不過,如果一段遺傳信息可能的生命週期很短的話,兩者的差異就不會很顯著。換個角度來看,每一個活著的生物個體從其胚胎發育期開始就是由一些基因建造出來的,而這些基因能夠追溯到許多許多代際以前的許多許多祖先個體身上。活著的生物繼承了這些曾經
幫助過許多許多祖先存活下來的基因,這就是為什麼活著的生物具備存活下去所需的一切, 並且能夠繁衍下去。它們所需的東西具體是什麼,是因物種不同而各異的—捕獵者或是獵物,寄生蟲或是宿主,水生或是陸生,棲息在地下或是森林的樹冠層—但是普遍性的原則仍是相同的。 本書的一個核心論點是由我的朋友,偉大的比爾·漢密爾頓提出並完善的。我至今仍在為他的離世感到哀痛。我們認為動物應該不僅僅要照料自己的孩子,而且還要照料其他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對此,有一個我很喜歡的簡潔的表述方式,就是“ 漢密爾頓法則”:如果一個利他性的基因能夠在種群中擴散開來,那麼必然滿足以下條件,即利他者的成本C 要小於受益者獲得的價值B 與兩者
之間的親緣度係數r 之積。這裡的r 是一個介於0 與1 之間的比例。對於同卵雙胞胎來說,r 的取值是1,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則是0.5,孫子孫女、異父或異母的兄弟姐妹, 以及同胞兄弟姐妹的孩子是0.25,同胞兄弟姐妹生出來的堂或表兄弟姐妹之間則是0.125。但什麼情況下r 是0 呢?在這種定義之下,0 的含義是什麼?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會更困難一些,但的確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自私的基因》第一版中沒有完全給予闡明。 0 並不意味著兩個個體沒有共同的基因。所有人類之間共用著超過99% 的基因,人與老鼠也有超過90% 相同的基因,與魚有四分之三相同的基因。這些相當高的比例令許多人對於親屬選擇產生了誤解
,其中甚至還包括一些傑出的科學家。但是上面這些數字並非是r 的含義。比如說我與我兄弟之間的r 值是0.5,那麼我與種群背景之中一個可能會與我競爭的任意成員之間的r 值就是0。為了對利他主義的進化進行理論化的分析,堂兄弟姐妹之間的r 值為0.125 只是在與種群參照背景(r = 0)相比較的情況下選取的。這裡的參照背景是指種群中其餘的個體,利他主義可能也曾在他們身上體現過:雖然面對食物和空間時是競爭對手,但面對物種的生存環境時是歷經久遠歷史的夥伴。這些數值,0.5 或是0.125 等,指代的是在親緣關係趨近於零的種群參照背景之上的額外的親緣關係。 威廉斯所定義的基因是一種可以計數的東西,你可以
隨著一個物種的代際更替去計算它的數量變化,這無關其分子層面上的本質是什麼。比如說,基因的本質是被基本呈惰性的“內含子”(會被翻譯機器忽略)分隔的一系列“外顯子”(被表達的部分),然而這一事實並不影響威廉斯所定義的基因。分子基因組學是一個迷人的領域,但是它並未對進化的“基因視角”產生巨大的衝擊,而這種視角正是這本書的中心主題。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換個說法:《自私的基因》的觀點很可能對於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也是能夠成立的,即便那些星球上的基因與DNA 毫無關係。不過,現代分子遺傳學的具體內容,以及關於DNA 的具體研究成果,是可以有辦法納入基因視角之中的。結果你會發現,它們實際上證明了我關於生命的
觀點的正確性,而非對其產生懷疑。對於這一點,我會稍後再繼續探討。而現在,我要換個跨度有點大的話題, 它始於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顯然能夠代表一大票類似的疑問。 你與伊莉莎白二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I)之間的親緣關係有多近?對我來說,我知道自己是她的十五重堂兄弟姐妹的孫輩。我們共同的祖先是第三代約克公爵理查·金雀花(Richard Plantagenet,1412— 1460)。理查的兒子之一是英王愛德華四世(King Edward IV),伊莉莎白女王是他的後代。理查還有一個兒子是克拉倫斯公爵喬治(George, 傳說是在一桶烈性白葡萄甜酒中淹死的),我是他的後代
。很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與女王的親緣關係其實比十五重還近,我亦如此,門口的郵遞員也是如此。有很多種方法可以讓我們成為某個人的遠房表親, 或者讓我們都成為彼此的親戚。 我知道自己是妻子的十二重堂兄弟姐妹的孫輩(共同祖先是喬治·黑斯廷,第一代亨廷頓伯爵,1488—1544),但是很有可能我們還能通過某種未知的不同方式成為血緣關係更近的親戚(從各自祖先查下來的不同路徑),而且絕對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讓我們成為血緣關係更遠的親戚。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你和女王可能既是九重堂兄弟姐妹的六世孫輩,又是二十重堂兄弟姐妹的玄孫輩,還是三十重堂兄弟姐妹的八世孫輩。我們所有人,無論生活在世界上的哪個地方,不僅僅是
彼此的遠房親戚,而且還有幾百種連接親緣關係的路徑。這只不過是用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們所有人都是種群的背景,我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指數r 趨近於零。我可以依照有據可查的一條路徑去計算自己與女王之間的r值,但是根據r 值的定義,最終算出來的數值會非常接近於零,因而完全起不了什麼作用。 導致所有這些令人頭昏腦漲的多重親緣關係的原因在於性。我們有兩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越往上越多,近乎天文數字。如果你不斷乘以2,一直計算到征服者威廉的年代,你的(以及我的、女王的、郵遞員的)祖先數量將至少是個十億數量級的數字,比當時全世界的人口數量還多。這個計算本身就證明,無論你是從哪裡來的,我們都共同擁有許多
祖先(如果回溯到足夠久遠的過去,我們的祖先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們彼此也是很多不同形式的親戚。 如果你不是從生物個體的視角(生物學家的傳統視角),而是從基因的視角(這一整本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來提倡這種視角)來看待親緣關係這件事情的話,所有這些複雜性就都不存在了。不要再問我與我的妻子(或郵遞員,或女王)有什麼樣的親緣關係,相反,要從單獨一個基因的視角來提問,比如我的藍眼基因:我的藍眼基因與郵遞員的藍眼基因有什麼關係?像ABO 血型系統這樣的多態性可以回溯到久遠的過去,甚至連猿類和猴子也有同樣的系統。站在人類A 型血的基因的立場上看,黑猩猩身上與之對應的基因是其近親,而人類的B 型血基因反而親
緣關係更遠。在Y 染色體上的SRY 基因決定著動物個體是否是雄性。我的SRY 基因會把一隻袋鼠的SRY 基因“ 看作”近親。 或者,我們還可以從線粒體的視角來看待親緣關係的問題。線粒體是充斥在我們細胞之中的小東西,攸關生死。它們是無性繁殖的,保留了自己殘存的基因組(它們與自由生活的細菌有極遠的親緣關係)。根據威廉斯的定義,一個線粒體的基因組可以被看作一個單一的“ 基因”。我們只能從母親那裡獲得線粒體。所以,如果我們想知道自己的線粒體與女王的線粒體有怎樣的親緣關係,那麼只會有一個答案。我們可能不知道那個答案是什麼,但是我們的確知道她的線粒體與你的線粒體之間成為親戚的方式只有一種,而非從整個身體
的視角來看時的幾百種不同方式。你可以一代一代回溯你的祖先,但是只能沿著母親這條線回溯, 你會得到一條單一的(線粒體的)細線,而非不斷分支的“ 整體生物家譜”。你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回溯女王的祖先,追蹤她的那條母系細線。遲早,這兩條線會彼此相遇,此時只要數數每條線上過了多少代,你就能輕易計算出你與女王的線粒體親緣關係了。 你能在線粒體上做的操作,理論上也可以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基因上重複,這就顯示出了基因視角與生物體視角的不同。從整個生物個體的視角來看,你有兩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等等。但是, 每個基因就像線粒體一樣,只有一位父母輩,一位祖父母輩,一位曾祖父母輩,等等。我有一個藍眼基因,
女王則有兩個。理論上,我們能夠回溯基因的代際,找到我的藍眼基因與女王的每一個藍眼基因之間的親緣關係。我們兩個基因的共同祖先被稱為“聚結點”。聚結分析已經成為遺傳學的一個繁盛分支,而且非常吸引人。你看出來了嗎?這與整本書都在宣揚的“基因視角”是多麼相得益彰啊!我們已經不是在談論利他主義了。基因視角在其他領域也能顯示出自己的力量,比如在尋找祖先這件事情上。 你甚至可以去分析一個生物個體的身體裡兩個等位基因之間的聚結點。查理斯王子也有藍色的眼睛,我們可以假定他的15 號染色體上有一對不同的藍眼等位基因。查理斯王子的兩個藍眼基因分別來自他的父母,這兩個基因之間有多近的親緣關係呢?對此,我們知道一個可
能的答案,而這僅僅是因為王室的家譜比我們大多數人的家譜記錄得更為詳盡。維多利亞女王也有藍眼,而查理斯王子可以有兩種方式算作維多利亞女王的後代:從他母親那邊通過國王愛德華七世來算,或從他父親那邊通過黑森的愛麗絲公主來算。有50% 的可能性,維多利亞的一個藍眼基因剝離出了兩個拷貝,一個給了她的兒子愛德華七世,另一個給了她的女兒愛麗絲公主。 這兩個子代基因更進一步的拷貝很容易一代代傳到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和菲力浦親王身上,從而在查理斯王子身上重新組合在一起。這就意味著,查理斯兩個基因的“ 聚結點”是維多利亞女王。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查理斯的兩個藍眼基因是否真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從統計學上來說,他的
很多對等位元基因肯定都會回溯到維多利亞女王身上聚結。同樣的推理也適用於你的一對對基因和我的一對對基因。即便我們可能沒有查理斯王子那樣清晰記錄下來的族譜可供查詢, 但是你的任何一對等位基因理論上也能找到它們的共同祖先,那就是它們從一個單一先祖基因上“剝離”開的聚結點。 下面要說的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雖然我無法找到自己任何一對特定等位基因的確切聚結點,但是理論上來說,遺傳學家們能夠對任何一個個體身上的所有對等位基因做聚結點的分析,考慮歷史上所有可能的親緣路徑(實際上不是所有的可能路徑,因為實在太多了,所以只能是抽取一個統計上的樣本),從而得出這個個體整個基因組的聚結模式。位於劍橋的桑格研究所的李
恒(Heng Li)和理查·德賓(Richard Durbin)發現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一個單一個體的基因組中所有成對等位元基因的聚結模式就可以給我們足夠多的資訊,讓我們得以重建其整個物種在之前歷史中的種群統計學細節,確定那些重要事件的發生時間。 在我們關於成對基因聚結的討論中,兩個等位基因中的一個來自父親,一個來自母親。這裡“基因”的含義比分子生物學家所說的基因更為靈活一些。實際上,你可以說聚結遺傳學家回歸到了一個概念上,有點類似於我之前所說的“ 染色體有點自私的一大部分以及更為自私的一小部分”。聚結分析研究的物件是一塊塊的DNA 序列,它可能比分子生物學家所理解的單個基因更大,也可能甚至
更小,但是它們仍舊能被視為彼此的親戚,是從一個有限數量的世代之前的共同祖先那裡“ 剝離”出來的。當一個(上述意義上的)基因“ 剝離”成為自己的兩個拷貝,並分別傳給兩個子女時,這兩個拷貝的後代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積累不同的突變。這些突變可能是“ 不會被注意到的”,因為它們不會表現為表型上的區別。 兩者之間突變的差異與分離之後經歷的時間是成正比的。這一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分子時鐘”,已經被生物學家們很好地利用起來了,可以測量巨大的時間跨度。此外,我們去計算親緣關係的這些成對基因不一定要有著相同的表型效應。我有一個來自父親的藍眼基因, 與之成對的等位基因則是來自母親的棕眼基因。雖然這些基因不同,
但它們必定在過去的某個時候有一個聚結點:在那個時刻,我父母的共同祖先的一個特定基因剝離成了兩個拷貝,分別傳給了這位祖先的兩個孩子。這次聚結(不同于維多利亞女王藍眼基因的兩個拷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從而讓這對基因有足夠長久的時間來積累差異,尤其是導致不同眼睛顏色的差異。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
為了解決堂兄弟定義 的問題,作者白春燕 這樣論述:
日治時期台灣在1920、1930年由知識階級參與演出的「新劇」或「文化劇」,受西方文明刺激產生的新文化運動影響而興起,其發展與台灣社會文化特質及歷史處境息息相關。自從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倡導新文化運動以來,台灣新劇運動開始發展,直到1937年進入皇民化戲劇時期之前為止。這段期間出現許多新劇社團,多數附屬於文化協會旗幟之下,少數是在最初受文化協會影響而成立,或主事者具文化協會會員身分,性質各異,但皆以戲劇改良及社會改革為目的,都屬於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共同建構台灣文化協會的演劇系譜。過去相關的研究成果已大致確認台灣新劇運動與政治社會運動互為表裡的事實,本論文則進一步從個人與劇團、劇團與
政治社會運動的社會網絡關係出發,辨識劇團的屬性及發展過程,試圖更完整、更細緻地釐清台灣新劇運動的全貌。本論文指出,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起於1921年,結束於1936年。在這個系譜的發軔時期,首先在1922年至1923年有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學生戲劇嘗試,接著在1923年冬天出現具組織性的新劇結社,之後全台各地劇團陸續出現。各劇團的成員大多是具有公學校基礎教育的知識階級,具有地緣性、學緣性的關係,在相同的身分階級或政治社會理念下集結而成。劇團之間因成員的交流或派別的合作,使戲劇養分具有支援、傳遞的連續性質。這個系譜裡的劇團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有關的劇團,皆附屬於政治社會運動團
體,受政治力的作用影響。愈左派的劇團,受政治壓制的力道愈強,消失得愈快;左傾程度較弱的劇團,則可以保持較久的戲劇活動。具體而言,新文協派的劇團大部分在1928年官方壓制下停止活動,而民眾黨派的劇團則晚至1931年民眾黨遭解散前後失去舞台。第二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無關的劇團,其中再依母會附屬團體的有無分為兩類。附屬型劇團以公益募款、社區營造為目的,以戲劇表演為母會團體服務。此類的劇團,不論是附屬型或非附屬型,都不具有政治社會運動色彩,未受到1928年及1931年兩波官方壓制影響,能夠在1930年代持續保有演出能量,直到1936年因戰爭時局變化而自然退場,使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走到終點。此時仍有
一些志在演出的劇團,在1937年轉型為皇民化劇團,戲劇精神與台灣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已不能納入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之中。從這個系譜可以看出台灣新劇運動是基於政治宣傳而誕生。亦即,台灣新劇運動是一批熱心政治的台灣青年受「新劇」這個新媒體所吸引,將西方現代戲劇的現實批判精神應用於現實中的政治社會運動,以達成思想宣傳的目的所發展出的戲劇運動。台灣文化劇、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的創始期都有這個相同的特點。不過,相較於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經過創始期之後發展出獨自的戲劇形態而進入成熟期,台灣文化劇因殖民政府的取締壓制,戲劇藝術的發展受到干擾中斷,未能發展出完整的戲劇形態,沒有機會進入成熟期。然而,許多不
具有政治色彩的劇團因未受打壓,在1930年代仍保有演出機會,使戲劇養分持續醞釀,甚至到了1940年代皇民化戲劇統制時期,短暫出現了一些出自台灣人之手、具有台灣民族主體意識的寫實主義戲劇。這些戲劇的出現,說明的是1921年以來的台灣新劇運動的道路雖然荊棘滿佈,但已播下足以開花結果的種子。因此,我們從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看出台灣新劇運動的意義是:它以新的載體傳播思想現代性,同時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也就是,1920、1930年的「新劇」或「文化劇」,是台灣新文化運動除了演講、報紙之外另一項宣傳利器,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上升期,發揮了文化啟蒙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使得因政
治社會運動而興起的新劇,未隨著政治社會運動的衰退而中斷,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下降期的1930年代,仍然保有演出能量,使新劇觀念及舞台經驗得到累積與傳承,並且從台灣人的主體性出發,對於戲劇進行再生產,創造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獨有的戲劇風貌。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為了解決堂兄弟定義 的問題,作者詹姆士.道斯 這樣論述:
二戰70年 人權論述大作 鮮明呈現極端的殘暴,傳遞疼痛 本書借鑒對中日戰爭中戰爭罪犯的第一手採訪,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帶領讀者進入種種駭人聽聞的罪行。但這本書所問的並不是戰爭罪犯這回事,而是企圖去貼近他們,進一步思考暴行是如何被觀看、如何被感受?促使暴行產生的原因又是什麼?如何才能停止暴行?然而,最終我們可能被迫承認,人類擁有難以回答的問題,並承認這些問題可能沒有令人安慰的答案。 解開「邪惡」的真相―― 邪惡,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 邪惡的樣貌既不橫眉怒目,也非青面獠牙。 其特質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 人們總是素樸而僥倖地
以為,邪惡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善良悲憫如我等,絕不可能成為惡;安分守己如我等,更不能成為惡的受害者。 但是萬一,萬一那天真的降臨,除了悲憤控訴或同流合汙,我們真的敢於抵抗邪惡所施加於的暴行嗎?戰時犯下「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戰犯、相信強暴婦女是種族清洗必要手段的聖戰士,以及被捕後露出詭異微笑的殺人兇手等,無一不是如同你我的平凡人,他們和我們一樣努力生活、遵守交通規則、渴望得到幸福和成就感……為什麼?為什麼做得出「那種事」? 或許,邪惡的特質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作者對二戰日本老兵進行第一手訪談,以小說家的筆法抽繹他們的戰時回
憶,串起了本書各主題之間的脈絡,但這些回憶只是一種人類情感的顯影劑,藉以還原「邪惡」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內隱的意涵。 作者試圖把所有關乎邪惡的討論聚焦在那些我們不忍卒睹、刻意忽視的黑暗角落——放大、拉近,強迫觀看,挑起了人們在面對歷史上的戰爭、屠殺、暴力時的一連串偏見與錯誤想像,再從觀者震驚、尷尬、不解等情緒中,將之一一拆解,加以釐清,賦予定義,並延伸至各個學術面向,進行開放性的嚴肅討論。 本書的寫作超出學院論述的邊界之外,論述結構更有別於以往類似主題的出版品,採回文形式呈現,未分章節,一氣呵成。正義不一定只站在哪一邊,如此跨界而綿密的討論,為的是處理「邪惡」這一巨大命題時能不
偏重任何一個片面的武斷。 討論範圍既廣且深―—從鄂蘭(Arendt)談到津巴多(Zimbardo),從凶殘談到原諒,從道德制約談到人性慾望,從「再現的弔詭」談到戰爭的淚水,內容擴及哲學、倫理學、宗教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美學等範疇,同時也觸及到人們在觀看暴力、陳述暴力時可能遭遇的道德倫理風險,特別是在現今社會,你我都可能成為暴力行為的觀者(或幫兇?),有些界線我們必須即刻釐清。 最後,作者提醒我們,當面對「邪惡」的拳頭如雨落下,唯一能做的最好還擊也許是「寬恕」。本書中那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將會怎樣影響我們的世界觀、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最後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端看我們的「同理心」能發
揮多大效用,此一困難的人性鑽探,將在閱畢本書後得到解答。 名人推薦 道斯對暴力進行了深度和範圍寬廣的沈思。他從鄂蘭(Arendt)談到津巴多(Zimbardo),從凶殘談到原諒,從再現的吊詭(paradoxes of representation)談到和戰爭的淚水(真誠或不真誠的淚水)。書中日本老兵所述說的故事讓人不得安寧。道斯一方面以社會科學家眼力掌握凶殘的成因,又以小說家的眼力抽繹出暴力對當事人的個人意義、自惠性和哲學蘊含。這是一種稀有的成就。轉述刑求者自白的著作不下一百五十部,但從未有一部帶有如此強烈的文學自覺。——賈禮(Darius Rejali),《刑求與民主》(Tortur
e and Democracy)作者 這部非同一般的書讓人驚恐、憤怒和困惑。道斯把我們帶進犯了「反人類罪行」罪犯的思想世界,同時又提醒我們,沒有若干互相信賴就不可能進入別人的心靈。《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與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格鬥(即設法從它看見的事情理出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道斯的凝視從不動搖。——費爾德曼(Noah R. Feldman),哈佛法學院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超出學院論述的邊界之外,其結構很多方面都與別不同。道斯不但鑽探了人可以有多凶殘,還以原創和近乎不能複製的方式探索了我們對那些行為不能見容於文明社會的人可有多大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哈帕姆(Geo
ffrey Harpham),國家人文學中心 作者簡介 詹姆士.道斯 James Dawes 劍橋大學哲學碩士,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哈佛大學院士學會青年院士,美國英語文學教授,擅長領域包括:反文化;人權:文學與語言理論;暴力與創傷;文學與哲學。其著作《惡人:普通人如何變成惡魔》(Evil Men, 2013)獲國際人權圖書獎;《好讓世界知道》(World May Know: Bearing Witness to Atrocity, 2007)入圍獨立出版圖書獎決選名單。另著有《語言的戰爭》(The Language of War, 2002)。不時在各大媒體(全國公共廣播電台、B
BC、保加利亞國家電台、《波士頓全球報》、《高等教育紀事報》和CNN網站等)亮相或撰稿。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共完成約近百本譯著,包括《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前言 《惡人》正文 參考書目 致謝 前言 本書要談的是凶殘:它長什麼樣子,
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有什麼方法或許可以防治。整件事情起於我和攝影師納德爾(Adam Nadel)到日本採訪一批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戰犯。他們年老衰弱,很多年過八旬,年輕時曾幹過最讓人髮指的惡行。他們最終全被俘虜,在戰犯營裡關了十年。他們給我看戰爭歲月的照片︰褪色黑白照裡那個年輕人穿著軍服,表情或自豪或害怕,或兇狠或稚嫩。看著自己的年輕自我,他們說他們看見的是虛空,是惡魔。 我參與人權工作多年,但之前從未訪談過加害者。事前我完全沒料到這些訪談會讓我暈頭轉向,更讓我嚇一大跳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自己竟開始以受訪者的眼睛看世界。本書的風格和結構都是為分享這種奇特經驗而設計。本
書不只是關於戰爭罪犯幹過些什麼,還是關於跟他們就近相處是什麼感覺。 以下,我會把本書要探問的問題歸結為五大群組,而它們也構成本書的一幅概念地圖。本書的推進方式是模仿一個變焦鏡頭的移動:先是用廣角鏡把整個畫面收入,然後用近鏡慢慢推進以顯示細部——這時細節雖已被擴大的焦點隱沒卻仍然鮮明,就像是凝視太陽太久在視網膜留下的印象。然後鏡頭會轉至另一個關懷重心。 在逐一處理以下五大群組的問題時,我將會突出它們內含的一些弔詭。詩人濟慈(John Keats)在一個不同脈絡提出過所謂的「守虛能耐」(negative capability):那是一種在面對不確定、神祕和疑惑時仍能保持敞開的能力,拒絕
把一切化約為熟悉的語彙和範疇而使之可為我們所控制。「守虛能耐」——還有它在文體領域的堂兄弟「錯置」(juxtaposition)——讓我們可以把弔詭經驗視為一些開放性問題,有時還可以讓我們在語言表達窮歇無靈之處經驗到意義。 1.書寫或閱讀一本這樣的書存在哪些道德風險?在觀看暴力和創傷性事件時,我們要如何方能懷抱尊重和關懷而不致流於看八卦的好奇心態?深邃的私人創傷要如何方能呈現於公共空間?這些問題的答案中心皆包含一個起到結構作用的弔詭︰創傷的弔詭。我們既有道德責任去再現(represent)創傷,亦有道德責任不這麼做。 2.如果我們打算一同經歷這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它們對我們有何用途?
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回答以下這類問題嗎:社會是怎樣把普通人變成惡魔?當事人會經歷什麼樣的心理過程?有鑑於這些惡魔往往是男人,性別在種族清洗上扮演著什麼角色?再一次,這些問題的答案皆是環繞著一些關鍵性弔詭旋轉,包括了「邪惡的弔詭」(「邪惡」既是妖魔和他者,卻又是平庸和人人皆幹得出來)和「責任的弔詭」(我們是自由和自我決定,同時又是環境的產物)。 3.把鏡頭拉回︰這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會怎樣影響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我們最後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我們對利他主義、超在(transcendence)甚至是「神」(the divine)的觀點?牽涉其中的是一些我們熟悉的弔詭,包括「利他主義的
弔詭」(利他主義既要求我們為利益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但我們利益他人時又往往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虛無主義的弔詭」(我們必須面對自己的無意義性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以及基督教版本的「惡的弔詭」(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如何能容許罪惡疾苦的存在?) 4.經歷過會震撼我們良知和動搖我們世界觀的暴戾殘忍之後,寬恕是可能的嗎?個人或國家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後還能指望獲得饒恕嗎?既然歷史本身就充滿謊言,而人的記憶力又總是不牢靠、自我保護和自利,你如何指望加害者能忠實自白?事實上,真相在戰爭、刑求和自白中有其位置嗎?有的話又是什麼位置?思考這一系列彼此相關的問題會驅使我們不斷回到「自白的弔詭」:自白
(confession)既是療癒所寄的文化形式,又是具有潛在破壞力的形式。 5.最後是最首要的問題。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倫理(ethics)。然則什麼又是更一般性的說故事倫理(ethics of storytelling)?對我來說,這裡牽涉的正是最難以排解的弔詭:書寫的弔詭。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必須培養出對別人的尊重和親密關係;然而,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又必須把他們非個人化,予以建構、擺布和展示。很多人會從事書寫或閱讀創傷故事這種艱難工作,是因為相信此舉可以提升人類尊嚴。說故事不只是人權維護(human rights advocacy)的最基本工作,並且是人類同理心
的最基本工作。但我們說出的故事真的可以改變什麼嗎?如果可以,帶來的又是哪一類改變?閱讀暴力性和創傷性事件時,我們真的可以懷抱尊重與關懷而不是看八卦的好奇心態嗎?當各位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將會發生些什麼? 你懷念你的老戰友嗎——就是那些跟你一起待到戰爭結束的人? 啊,會,我懷念他們。你知道,他們大部分人都像兄弟。真的。他們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像…… 對,我們一起出生入死。我們一起經歷過的事情比親兄弟還多。對,我懷念他們。當然懷念。 * 每一次,我都會送給受訪者一小包明尼蘇達州的野生稻米。每一次,我一開始都會表現得笨嘴拙舌,反覆半鞠躬道歉,為同一件事情自嘲︰我連「很高興跟你會面
」乃至「謝謝」之類的簡單日語都說不好。他們聽了會面露微笑(我敢說他們會為此驚訝)。在在看來,我每次一開始就先自暴其短是件好事。 每天早上,我和攝影師會到飯店外面喝咖啡和吃酥餅。每天傍晚,女譯員會帶我們去找消遣:看歌舞伎,看武術表演,吃最好吃而不昂貴的壽司,去她最喜歡的老酒館喝兩杯。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唯獨不談那些我們採訪過的老兵。 * 為什麼我會幹得出那樣的事?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本來只是個農家子弟,一個在農民家庭長大的人。這是我後來會思索的問題。對,你最終一定會覺得奇怪。唉,我不是個會幹出那種事的人。 * 直至今晚以前,我不算是看過真正的格鬥。日本有些武術表演很文雅,像是液體舞(liq
uid dances),但今晚的表演卻是貨真價實的打鬥。其中一方眼見就要勝出。他把另一個男人壓倒在草蓆上,用拳頭狠狠揍對方的頭,一次又一次。觀眾會隨著每一下拳頭悶聲發出集體呻吟。挨揍的那個男人想必痛得厲害,但臉上卻看不見任何表情。揍他的那個男人反而表情豐富,像是憤怒或害怕——但我說不出來是憤怒還是害怕。 因為忙著跟攝影師和女譯員交談,我過了很久才離場,並因此跟先前兩位格鬥者在電梯裡湊巧遇上。這時我才看出來,他們其實不算是男人,只算是大孩子。我訝異於我的身高比他們高。但更讓我震撼的是看見他們站在一起,有說有笑。從這個近距離,我可以看見敗方的臉上破了皮︰想必是被草蓆擦傷。基於什麼理由,我對他生起悲
憫之心。我很想湊近問他:經歷過方才的激烈打鬥,你是怎樣回到正常生活的?
齋醮在台灣發展演變之研究一兼論台北碧潭地區四大古寺院導師之卡理斯瑪現象
為了解決堂兄弟定義 的問題,作者陳紀南 這樣論述:
當人類遭遇疑惑、困苦、煩惱時,就會有內心的思維,運用概念來判斷、推理,從感官知覺的認識,加上身外的法界、科學技術不斷的研究,期望證明一切事物的本質和法則。然而人類肉身的感官知覺和當今的先進科學技術卻仍然有很多無法超越的極限;尤其是超自然現象的迷惑,只有依賴宗教的祈禱祭祀來安心立命了。 在地理上,臺灣島四面環海,雖然是位於大國邊陲之海中,但自從東西洋各國貿易、文化等交流活動以海路為主後,卻因處於交通要地而登上國際舞台。 歷史上隨著政權迭次,新政策、新移民、新宗教等登陸臺灣後的融合影響,自然形成了本土意識的傳統文化,尤其是本土民俗宗教與佛教的淵源。 嘗試釐清在台灣,自明末清初以
來,宗教上屬主流,奉行祭拜釋迦牟尼佛、觀音佛祖等與佛教有淵源比較特殊之齋教團體,主要為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三派,隨著時代潮流,政權移轉,意識形態之利害關係,因而與佛教禪宗四大名山法脈等古寺院的互動淵源探討。 齋教發展進入日治時代以後,由於日本佛教的引入,在其逐漸掌控並主導台灣宗教發展的情形下,導致了許多的齋友陸續剃髮出家,成為佛教徒。靈泉禪寺的善慧法師、凌雲禪寺的本圓法師、超峰寺的永定法師,法雲禪寺的妙果法師等,都曾經是齋教徒的一員,他們都成為帶領該派系開花結果展露頭角,甚至是台灣佛教界登峰造極的開創者。 故擬從碧潭地區四大古寺院具體的宗教場域、人物和思想來入手,以釐清其間之差別點;
其脈絡之演變和各宗教派系的導師、領導人之卡理斯瑪(Charisma) (カリスマ)現象;研究在不同時空背景、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影響,展開而形成佛教新興團體的趨勢,作為本論文之研究範圍,期望進一步對應《大乘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相關經文中,真實義的研究。